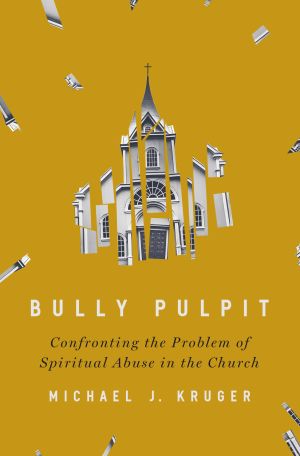
【讲台霸凌】第四章
尸体的踪迹
– 为什么教会不阻止霸凌领袖呢
迈克尔·J·克鲁格/白帆译
恶魔是真实存在的…它们住在我们内心,有时会获胜。-斯蒂芬·金
1986 年,在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电影《异形》中,主角雷普利(西格妮·韦弗饰演)发现了一个名叫纽特的小女孩,她是 LV-426 星球上人类殖民地的最后幸存者。她的父母和她认识的每个人都被可怕的外星生物消灭了。当这个受到创伤的女孩终于开始说话后,她问了里普利这个富有洞察力和悲剧性的问题:“妈妈总是说没有恶魔——没有真正的恶魔——但有……他们为什么要告诉小孩子这些呢?”
孩子们有一种单刀直入的能力,会问成年人喜欢回避的问题。如果世界上有坏人,我们为什么要假装没有呢?我想,我们可能会像雷普利在电影中那样回答:“大多数时候是真的。”换句话说,既然大多数人都是好人,我们就不要在意少数人的不好。
有些教会对属灵虐待有这样的心态:既然属灵虐待的牧师很少见,我们就不要谈论这个问题,就假装他们不存在。当然,问题是,他们确实存在。正如耶稣所教导的,有时,看似好人,实际上是坏人:“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太7:15)。
换句话说,要警惕恶魔。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对“恶魔”这个词来形容霸凌牧师感到犹豫。也许有人会说,他们肯定没那么糟糕。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太严厉了?好吧,如果有人更喜欢“贪婪的狼”,那完全没问题(尽管我不确定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差异)。但我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使用“恶魔”一词,即指霸凌牧师经常发生的现实有两个侧面,就像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著名小说《化身博士与海德奇案》中的主角一样,一面是温暖和善良(面对大多数人的时候),另一面是残酷和黑暗(只有受害者才能看到)。就像史蒂文森的小说中一样,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同一个人可以兼有两种面具的事实。
这就引出了本章的主题。如果我们要解决属灵虐待牧师的问题——海德斯先生就在我们中间,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最好承认他们的存在,并学会如何发现他们。但是——这是一个可悲的现实——教会似乎通常不太擅长这样做,不擅长捕捉恶魔。
在一个又一个的虐待故事中,同样的悲惨事件不断上演。这位虐待牧师多年来,一直有破坏性行为,直到有人终于勇气发声。但即使以后,大多数教会什么也不做。 (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有些教会将攻击发声的人。)即使教会做了一些事情,也往往是半心半意、不充分的回应。当罕见的教会最终因虐待而罢免一位牧师时,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采取行动?为什么你能容忍这种行为长达二十五呢年?
我们问这些问题是因为有证据——大量的证据—揭露这些牧师的破坏性行为。查克·德格罗特(Chuck DeGroat)在他的著作《当自恋来到教会时》(When Narcissism Comes to Church)中指出,这样的牧师常常会留下“关系碎片场”。他观察到:“通常,在自恋牧师被公开曝光之前,会有多年痛苦的小遭遇被掩盖。 这些牧师有伤害同工的记录,最终,通常是在很多年之后,这种情况就会追上他们。这是一眼还看不出来的罪恶迹象,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变得清晰可见。正如提摩太前书 5 章 24 节所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
简而言之,施虐的牧师会在身后留下‘尸体的踪迹’。 这就是恶魔所做的。那为什么教堂看不到尸体的踪迹呢?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些点联系起来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一个施虐的牧师,而在于,教会文化助长了(有意或无意)虐待行为。
或者,正如奥克利和金蒙德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倾向于]关注坏苹果以及它的问题所在,而不是关注存放它的木桶。”本章中,我们将关注木桶。
责任结构不充分:什么尸体?
一些教堂看不到尸体的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尸体被隐藏起来。可以说,霸凌牧师把他们埋在后院,而教会的问责结构不完善,意味着人们无法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不想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尸体以多种方式隐藏。首先,许多牧师虐待的受害者被压制或被迫离开。在一个又一个属灵虐待的故事中,遭受虐待的人被孤立,并被赶出了该事工。人们看不到整体模式,因虐待的受害者为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敢发声,就悄悄离开了,而那个施虐的牧师却留下来了。
如果施虐的牧师仍然存在,那么,他就可以控制叙事。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受害者有时会因整个事件而受到指责。他们才是问题所在,而不是施虐的牧师。
其次,施虐牧师破坏关系的模式往往不会向更大的领导机构透露,当然也不会向整个教会透露,只是在某些委员会或小组内传达。韦德·马伦 (Wade Mullen) 观察到,“许多受害者发现,他们向某个组织提出的虐待报告是由专门的团队处理的,或者是由一小群执事会成员处理,而不是与整个执事会共享。”
现在,一定程度的保密是可以理解,也是明智的。所有的不满都不应该在全教会面前宣泄出来。也就是说,一些教会已经学会了“管理”虐待牧师的关系碎片场,其方式与现代政客没什么不同——它被隐藏在人事委员会中,以至于永远见不到阳光。这种方法非常有效,有时甚至连牧师自己的长老都不知道这种关系的破裂已经发展成长期模式,或者至少不知道它有多深、多广。
第三,即使虐待受害者挺身而出,并被领导机构听到其声音,但问题也常常被淡化和最小化——这被视为任何部门都不可避免的冲突。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嗯,那只是鲍勃牧师。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或者通过坚持认为,这正是当你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时会发生的事,以此来将问题最小化。我们在《使徒行传 29》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蒂米斯 (Steve Timmis) 的案例中,看到这种反应,他最终因属灵虐待而被解雇。他的捍卫者表示,这些冲突仅仅是由于“领导风格的冲突”或“被强势领袖激怒”。
像这样的最小化模式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它部分正确。每个事工都有一些冲突。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冲突就是教会的一部分。
但是霸凌牧师有一些不同,他的关系碎片场不仅在冲突数量上不同,而且在冲突深度上也不同。通常,他身后的生命都被真正摧毁了。许多人离开了事工,也有许多人则完全放弃了基督教信仰。此外,施虐的牧师常常存在未解决的冲突,他们通常与许多以前共事的人疏远。
一旦出现这种模式,教会领袖就需要进行计算。所有这些冲突都有一个共同点:牧师。到底是这些人都有问题,还是牧师自己有问题呢?
可悲的是,有时,长老们看不到尸体,只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尽管后院挖开了所有的洞,他们只是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切都已经好起来。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的神学观点不正确:他们认为这样的恶魔不存在——至少在他们的教会里不存在。
对堕落的错误看法:没有恶魔
改革宗福音派经常谈论全然堕落的教义——罪比我们意识到的更深刻、更有害,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行动、思想、意志)。虽然每个人都没犯什么大罪,但每个人——甚至牧师——都有可能犯下严重的邪恶罪行。
尽管许多教会在纸面上确认了这一重要教义,但当涉及到属灵虐待的情况时,就很快会被遗忘。一旦受害者有勇气说出虐待行为,通常会遇到齐声反驳,比如:“我认识这位牧师,他永远不会这样做”,或者“这位牧师多年来已祝福并帮助了无数人。他永远不可能做这样的事。”领导层没有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仔细调查,而是认为这种虐待是不太可能的存在,因此不太深追事情的真实状态。
换句话说,恶魔不存在(至少在我们的教会里不存在)。
具有悲剧性的讽刺意义是,虐待牧师的捍卫者经常对受害者的正直和品格提出质疑,暗示他们是在污蔑或诽谤领袖的“好名声”。因此,当涉及到牧师时,全然堕落的教义被遗忘了,但当涉及到受害者时,却被记起了。
拉维·撒迦利亚被揭露之事告诉我们,即使是最受尊敬和爱戴的领袖,也有可能行出难以形容的堕落。撒迦利亚的捍卫者辩称,他永远不能、也永远不会这样施暴。但不乏证据表明,他的确如此行。尽管存在可疑的短信、不可靠的解释以及多名原告的证词,但撒迦利亚的捍卫者仍然支持他们的领袖。
如何解释教会和基督教组织忽视彻底堕落的影响,并为他们的领袖辩护的倾向,即使有具体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畅销书《与陌生人交谈》中,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格拉德威尔列出了许多备受瞩目的刑事案件,包括杰里·桑达斯基和拉里·纳萨尔的性虐待案件,并表明,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犯罪者有罪,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假定为无罪。为什么?只因所谓的真理默认理论。当人们在互动时,“我们默认真理:我们的操作假设是,与我们打交道的人是诚实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假设并不是一件坏事。格拉德威尔认为,人类默认真理,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做,才能在社会中合理有效运作。你能想象,如果每个人都经常怀疑、质疑和猜疑别人以及其每一个真理主张吗?这将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更不用说效率低下了。
但问题更大了。格拉德威尔指出,除了假设人们通常说真话之外,人们还常常错误地认为自己擅长发现不说真话的人。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评估人们的举止、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确定他们是否在说谎。但统计数据却恰恰相反。格拉德威尔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说明即使是执法人员(警察、法官和中央情报局特工)也无法有效识别坏人。格拉德威尔认为,我们假设大多数人都在说真话,而对识别撒谎者的能力过于自信,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在识别人的欺骗性方面提出一个严重问题。
但问题变得更糟。格拉德威尔指出了这些案例中的第三个因素:当我们被迫相信坏人的一些真正困难时,就特别不擅长发现这些坏人。他写道,“当我们被迫在两种选择之间做选择时,对真理的默认就成为一个问题,其中一种是可能的,另一种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是否更容易相信一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人像杰里·桑达斯基这样,在几十年里性侵了许多十几岁的男孩,还是更容易相信这只是一场淋浴间打闹、一场大大的误会呢?后者更容易让人接受。我们是否更容易相信,像拉里·纳萨尔这样受人尊敬的奥运队队医是一个可怕的性侵者,或者有些女孩误解了骨盆检查的含义?同样,许多人发现,后者更容易被接受。
格拉德威尔的研究也适用于教会中的属灵虐待。教会法庭——长老会、执事委员会——常常认为,他们善于发现不诚实、欺骗性的牧师。但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默认面前的人说的是实话,特别是如果这个人有着长期看似忠诚的事工记录。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困境:更有可能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牧师一直在专横地虐待、霸凌他的羊群,还是人们过于敏感,被一位强势的领袖激怒了?
如果评估被指控牧师的人认识牧师本人(教会法庭上几乎总是如此),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是这样,他们很可能已经对牧师评价很高。为什么?因为恶霸不会欺负所有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不会持续太久。霸凌者很少横向或向上欺凌。他们几乎总是欺负下面的人。因此,牧师常常对评价他的人——他的同辈——非常好。
由于全然堕落的教义已经退居二线,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正如所指出的,属灵虐待的牧师几乎总是有两面人:一面是迷人、亲切、讨人喜欢。但另一面可能是专横、高压、具有威胁性——同样,就像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一样。他们对谁能看到他们的哪一面是有选择性的。在很多方面,施虐的牧师就像施虐的父母一样。有时,父母对孩子是仁慈和爱怜的,有时却是残酷和具有报复性。他们在两个角色之间来回切换。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坏人就在面前时,我们却无法看到问题吗?至少在原则上,对全然堕落的神学信仰应该有所帮助。如果定期教导这一教义,应该会使任何个人和任何教会法庭都面临自称为基督徒的可能性,甚至是牧师,可能会犯下可怕的罪。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假设被告有罪,仅仅意味着这些指控不排除其可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会进行合法的调查。
但我们还可以做更多。格拉德威尔指出,某种罕见的个体并不是天生就认为每个人都是诚实的。某种性格类型是违背常理的——格拉德威尔称之为“说真话的人”。这些人“不属于现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脱口而出令人难以忽视的事实,或质疑我们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故事《皇帝的新装》中,小男孩是说真话的人,而其他人都在和裸体的国王一起玩耍,男孩脱口而出:“看看国王!他什么都没穿!”
大多数长老会、教会法庭和基督教事工的执事会都是由内部人士组成,而不是来自教会普通会众,他们通常由领袖的亲密同工,甚至是家人组成。那么,他们怎样才能客观地追究这位领袖的责任呢?这与警察追究其他警察过度执法是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因此,真正的问责很难实现。
这些团体需要的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也许是几个。这些基督教组织是否有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其领导结构,以纳入“不属于现有社会等级制度”的局外人?我们将在第七章进一步探讨这种可能的重组。
对恩典的误解:每个人都是恶魔
基督教的核心始终是关于恩典。保罗说得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 2:8-9)。近年来,特别是在改革宗、福音派圈子里,人们对恩典产生了新的关注。许多人呼吁“以恩典为中心”的讲道,重点不是我们的好行为,而是基督所完成的工作。这是一件好事。
但为了强调这种恩典的美丽,有些人采取了额外的措施。既然我们都是靠恩典得救的绝望罪人,那么,我们就不能区分罪的等级。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听到“所有罪,都是平等的”或““我们都是同样的罪人。”这样的话语是为了维护恩典;也就是说,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好。
现在,“所有罪,都是平等的”,这句话有部分正确,这取决于一个人的意思。如果有人用这句话,只是为了表明任何罪都足以使我们与神隔绝并招致祂的愤怒,就是正确的。神是如此圣洁,任何违反祂律法的行为,无论在我们看来多么微不足道,都是值得祂公义审判的罪。
但这并不是该短语的唯一使用方式。有人则用它来“消除”所有罪恶,使之无法彼此区分。或换句话说,它把所有人都描绘成同样邪恶。如果所有的罪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犯了罪,那么,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圣洁。在一个对“平等”着迷的世界里,这个词的这种用法特别有吸引力。让每个人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无差别的群体。
换句话说,这种对恩典的理解,要求我们相信自己都是恶魔。
但这种信念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其一,说所有的罪都是一样的,就是将罪的后果与罪的可憎性混为一谈。虽然所有罪的影响都是相同的(使我们与神隔绝),但它们并非同样都令人发指。圣经清楚地区分了不同的罪。某些罪的影响更为严重(哥林多前书 6:18)、罪责(罗马书 1:21-32)、应有的审判(彼得后书 2:17;马可福音 9:42;雅各书 3:1),以及一个人是否有资格从事事奉(提摩太前书 3:1-7)。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恩典的误解被用来为霸凌领袖辩护。有人认为,如果我们都是平等的罪人,就应该给霸凌牧师一个机会。他们是罪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如果不这么说,我们就会把自己放在对牧师审判的位置,让自己比他人更正义。相反,我们需要“向霸凌牧师展示恩典”。
可悲的是,这种对恩典的误解常常被归咎于受害者自己。他们因“不宽容”、“心怀怨恨”或(我们再说一遍)“不表现出恩典”而受到指责。
不难看出,这种神学错误有多么严重,让受害者觉得自己有罪,好像他们的铁石心肠阻碍了“和解”,完全忽视了虐待行为本身的可恶性,忘记了有些罪比其他罪更严重,有些罪人比其他罪人更坏。正如第三章所示,牧羊人虐待羊群是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这种对恩典的滥用,忽视了圣经中所有关于维护公义和正义,以及保护无辜者的段落。
可悲的是,另一个对恩典的误解被用来为施暴的牧师辩护,并进一步伤害受害者。有人认为,如果我们都同样有罪,就必定意味着,施虐的牧师和受害者对冲突负有同样的责任。对恩典的错误理解被用来淡化虐待的可恶性,并加剧受害者的罪恶,无论这些罪恶是什么。
我们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要对冲突双方“公平”。但有时,我们认为公平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双方承担同等的责任。否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找出真正的罪魁祸首。当我们已经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时,为什么还要费心去调查呢?告诉双方承认他们(同等)的罪,并找到相处之道,这要容易得多,而且在许多人看来,甚至更属灵。
因此,长老会有时会发表诸如“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罪”或“双方都有责任”之类的声明,把虐待变成了纯粹的关系冲突,与保罗和巴拿巴的分歧没有什么不同。
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是说,虐待的受害者不是罪人。他们是。我也不是说,受害者永远不会做错事,他们会错。但正如詹妮弗·米歇尔·格林伯格所说:“每个人都是罪人,但并非每个人都是施虐者。”
对和解的错误看法:与恶魔见面吧!
大多数执事会或管理机构不喜欢团队分裂。像大多数基督徒一样,他们希望看到争端迅速得到解决——这很好。事实上,现在似乎有比以往更多寻求和睦的部门。但这种建立和平的渴望,有时会导致教会匆忙让虐待受害者与施虐者和解,这是一种病态考量。因为教会经常将整个问题仅仅视为“冲突”,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专注于正义或问责制,而只需将受虐待者和施虐者放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有罪,问题就解决了。
也就是说,人们只需要与恶魔见面即可。
但这种做法令人深感担忧。虐待案件不仅仅是冲突,而是落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里,就相当于丈夫殴打妻子,然后和事佬告诉夫妻俩只需要做婚姻咨询,在那里,他们都承认自己有罪。但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然,妻子也是罪人。但无论她犯了什么罪,也不能为丈夫的虐待做辩护,也不应减少教会优先解决虐待行为的必要性。
正是这个错误,使得朱迪·戴布勒的和解事工变得如此悲惨。 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戴布勒应该是教会以圣经方式来解决冲突的主要领袖, 但她的和解方法却常常绕过那种会导致真正问责的事实调查,而是假设双方都同样有错为基点,来展开和解。正如《今日基督教》报道的那样,“她并没有把客观地描述事实作为首要任务……即使调解是因虐待指控而促成的。和解倡导者表示,相互认罪并不是应对不公正行为的适当起点。”
关于和解的正确方法,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将在第 5 章讨论马太福音 18 章)。目前,当教会寻求霸凌牧师与受害者之间的和解时,需要牢记以下几项原则:
首先,不应要求受害者与施暴的牧师会面,除非他已被追究责任。和解的基础始终从所发生事件真相开始,并对所发生事件的追责。担责是教会的工作,而非是受害者的。如果教会未能提供这种担责和保护,却坚持让受害者与施虐者会面,这就把重担转嫁到受害者身上。教会正在让受害者做教会自己没有做的事情。现在,受害者必须证明自己的受虐情况,却得不到教会的保护或帮助。这种情况为施虐者提供了更多攻击受害者的机会,实质上是再次虐待他们。
其次,受害者不应该会见施暴的牧师,除非牧师真正悔改。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教会确实追究了一名霸凌牧师的责任,但该牧师仍目中无人,且不愿悔改。但除非有真正的悔改,否则不可能有符合圣经的和解:“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路加福音17:3)。在这种情况下,虐待的受害者应该等到教会确定牧师已经真正悔改,仅仅声称悔改都不够,他必须向能够正确评估此事的管理机构表示悔改。
第三,受害者在情感和属灵上做好准备之前,也不应该与霸凌牧师见面。即使施虐者被追责并悔罪,也不意味着必须立即召开和解会议。许多虐待受害者都受到深深的创伤,以至于他们很难与施虐者在一起,直到真正的治愈发生。这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如果虐待的受害者拒绝见面,顽固不化的牧师可能会将受害者描绘成不宽容,且不愿意和解的人。他将占据道德制高点,让自己成为和平缔造者,让自己成为心怀怨恨的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在满足指导方针之前,教会甚至不能要求受害者与施虐者会面。这样,阻止聚会举行的就是教会,而不是受害者。
J·R·R·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双塔》(The Two Towers)中的一个场景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与一位顽固不化、滥用职权的领袖缔造和平的危险。在巫师萨鲁曼毁灭性的背叛之后,他终于遇到了甘道夫和洛汗国王希奥顿。尽管萨鲁曼犯下了令人发指、难以形容的暴行,但他并不承认自己任何过错,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与此同时——这是关键——他仍然想要与那些被他伤害的人交换和解协议。他要的是所有施虐的领袖都想要的:没有悔改和问责的和平。
托尔金如此准确地描绘了一个虐待领袖的语气和态度,这是值得注意的。当萨鲁曼对希奥顿说话时——曾试图将国王连同他的子民一起消灭——但此时,他给人的印象是善良、通情达理、平和:“你为什么不以朋友的身份来?我非常想见到你。”然后,他提出了和平:“我说,希奥顿国王:我们可以拥有和平和友谊吗?你和我吗?这是我们的权柄。”当他与甘道夫交谈时,萨鲁曼邀请他进行一场和平对话:“为了共同利益,我愿意纠正过去来接纳你。你不跟我商量一下吗?你不来吗?”
在所有这些陈述中——尽管看起来流畅而迷人——请注意,没有人承认有罪或做过错事。相反,萨鲁曼做了一些虐待领袖所做的事情:他把自己描绘成真正的受害者。他翻转剧本,让自己成为悲伤的一方:“尽管我受到了伤害,但洛汗人,唉!虽然我曾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我还是会救你。”当他与甘道夫交谈时,他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过,而是指出了甘道夫的罪过:“你很骄傲,不喜欢建议。” 换句话说,都是别人的错。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萨鲁曼甜言蜜语,希奥顿和甘道夫并没有被愚弄。他们不进入萨鲁曼的房间来促成和平协议。希奥顿很直白地说:“当你和你所做的都灭亡时,我们就会享有和平… 。萨鲁曼,你是个骗子,有一颗败坏的心。”同样,甘道夫也没有接受会面的邀请:“不,我想,我不会来。但听着,萨鲁曼,最后一次!你不愿谦卑下来吗?”甘道夫没有按照萨鲁曼的条件见面,而是简单地呼吁萨鲁曼悔改——并且真诚而诚恳地懊悔。但是,像大多数滥用权力的领袖一样,萨鲁曼不会心软。因此,甘道夫解除了他的职务:“萨鲁曼,你变成了一个傻瓜,但又很可怜。你可能仍然远离愚蠢和邪恶,并一直在服务。但你选择留下来… 。我将你逐出了修会和议会。”
结论
当执事会或基督教组织面临牧师或领袖虐待的指控时,我们需要意识到,他们可能已经有了以下假设:(1)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什么尸体?); (2)这位牧师看上去是个诚实、善良的人,是我们所认识和喜爱的(没有恶魔); (3)每个人都是可怕的罪人,各方都必须受到指责(每个人都是恶魔); (4)不需要问责,因为只要双方见面(只要与恶魔会面)就可以解决冲突。
考虑到这些假设,再加上大多数霸凌牧师所采用的广泛而有力的防御策略,我们面临着一个相当令人担忧的含义:在目前的系统下,要对一位牧师进行属灵虐待定罪是极其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案件特别严重,且有大量的外部证据(视频、录音、电子邮件),否则,属灵虐待牧师不太可能因受害者的证词而受到指控,让教会法庭了解真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场艰苦的战斗。
显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如果我们要与教会中的虐待作斗争,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仅是导致其不受制止的神学错误。我们必须还要了解施虐者及其支持者为自己的虐待行为辩护所采用的一系列策略。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主题。
